周易中的“际遇说”,相邻的属性不同的两个爻之间联系
“际遇说”亦是对相邻的属性不同的两个爻之间联系的说明。当阴爻与阳爻相邻,二者又不是明显的乘、顺联系时,则往往从“际”或“遇”的角度说明之。“际”指毗邻、交代,“遇”亦是相遇、相接之意,二者的意思不同不大。“际遇说”与“乘顺说”相比,前者不像后者那样有着鲜明的褒贬色彩,而只是对相邻两爻不同属性状况的一种提示,以引起人们的留意。如《垢•彖》:“‘娠’,遇也,柔遇刚也”,指初六与九二相遇。再如《睽•九二•小象》:“‘遇主于巷’,未失道也”,《睽.六三•小象》:“‘无初有终’,遇刚也。”崔觐注曰:“遇者,不期而会。”①可见《小象》所谓“遇主”“遇刚”指九二与六三相遇。又如《解•初六•小象》:“刚柔之际,义无咎也”,指初六与九二交代。又如《坎•六四•小象》:“‘樽酒簋贰’,刚柔际也”,指六四与九五交代。又如《蒙•九二•小象》:“‘子克家’,刚柔接也”,指九二与六三交代。又如《鼎•上九•小象》:“‘玉弦’在上,刚柔节也”,指六五与上九交代。又如《泰•九三•小象》:“‘无往不复’,天地际也”,指九三与六四交代。
以上是《彖》《小象》爻位说之大约,可见《彖》《小象》在解《易》思维与编制上有着激烈的一致性,故它们的作者或是同一个人,或是出于前后承继的易学世家或师徒。 —
再谈谈《大象》。经过陈说上下二体卦象的方法来说明一卦的卦名,并不是战国时期易学的中心问题,早在春秋时期人们就以卦象说明卦名,如史墨曰“雷乘乾曰《大壮》”。也就是说,《大象》作者创造的意图在于《大象》诸条的后半部分,即从卦象、卦名中引申出经验、品德、伦理和政治等方面的含义。如:
山下出泉,蒙;正人以果行育德。
火在天上,大有;正人以遏恶扬善,顺天休命。
天在山中,大畜;正人以多识前言往行,以畜其德。
山下有泽,咸;正人以虚受人。
雷风,恒;正人以立不易方。
山下有泽,损;正人以惩忿制欲。
关于《大象》的价值趋向和学派性质,前人已经作了不少的探讨,基本上可以看作先秦儒家政治与伦理学说的教科书,可以说,《大象》是易学彻底儒学化的一个产品。崔述在《洙泗考信录》中指出,《大象》有引用曾子之言的当地:
《论语》云:“曾子曰:‘正人思不出其位。’”今《象传》亦载此文。果《传》文在前与,记者固当见之,曾子虽尝述之,不得遂认为曾子所自言;而《传》之名言甚多,曾子亦未必独节此语而述之。然则是作《传》者往往旁采古人之言以足成之,但取有合卦义.,不必皆自己出。既釆曾子之语,必曾子今后之人之所为,非孔子所作也。®
刘大钧先生也指出《大象》有些当地显然是发挥曾子之言,如《益•大象》“正人以见善则迁,有过则改”,《震•大象》“正人以惊骇修省”,《蹇•大象》“正人以反身修德”,《咸•大象》“正人以虚受人”等处,与曾子在《论语》中表现出的自我自省的认识很一致。②
《大象》“惊骇修省”的认识,对《中庸》有所影响。如《中庸》:“道也者,不行须臾离也,可离非道也。是故正人戒慎乎其所不睹,恐惊乎其所不闻。莫见乎隐,莫显乎微,故正人慎其独也。”《大过•大象》:“泽灭木,大过;正人以独立不惧,遁世无闷。”《大象》“遁世无闷”的精力,对《中庸》《白话》也有影响。《中庸》:“正人依乎中庸,遁世不见知而不悔。唯圣者能之。”《白话》:“不易乎世,不成乎名,遁世无闷,不见是而无闷。乐则行之,忧则违之,确乎其不行拔,潜龙也。”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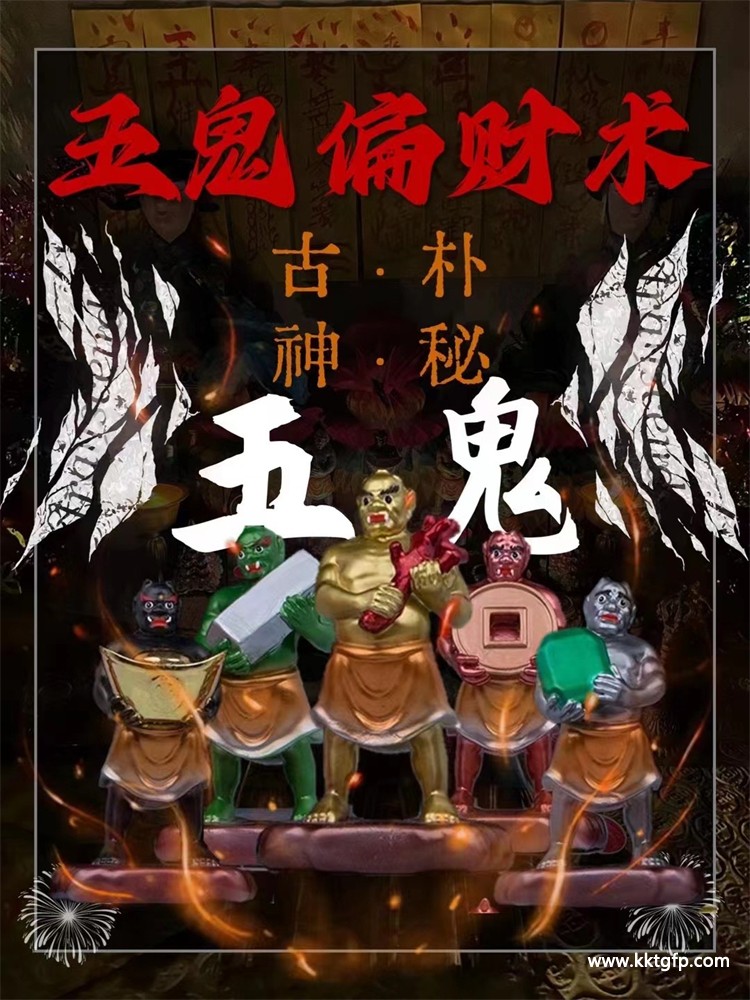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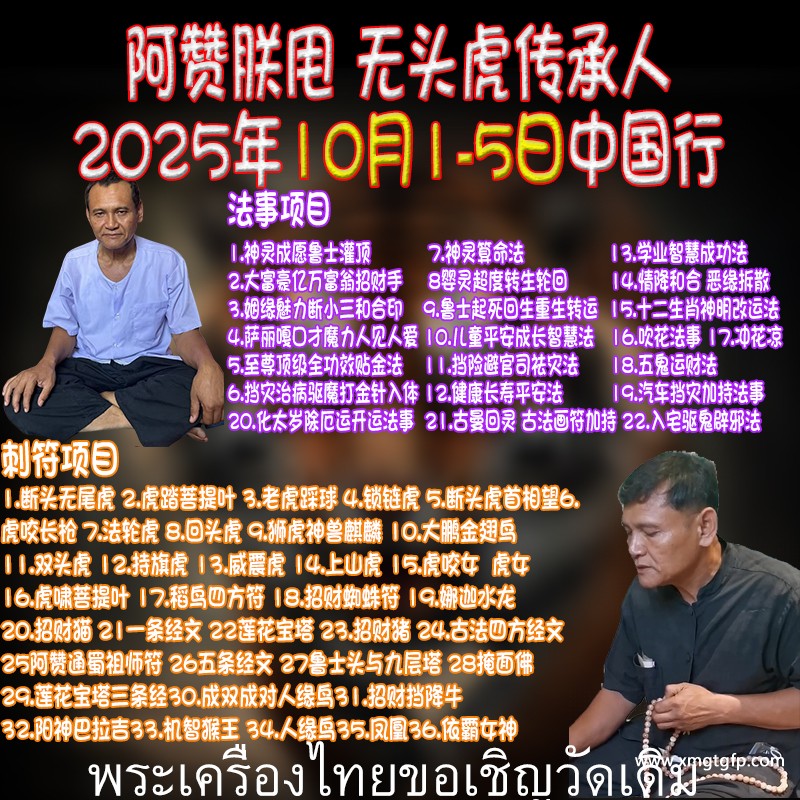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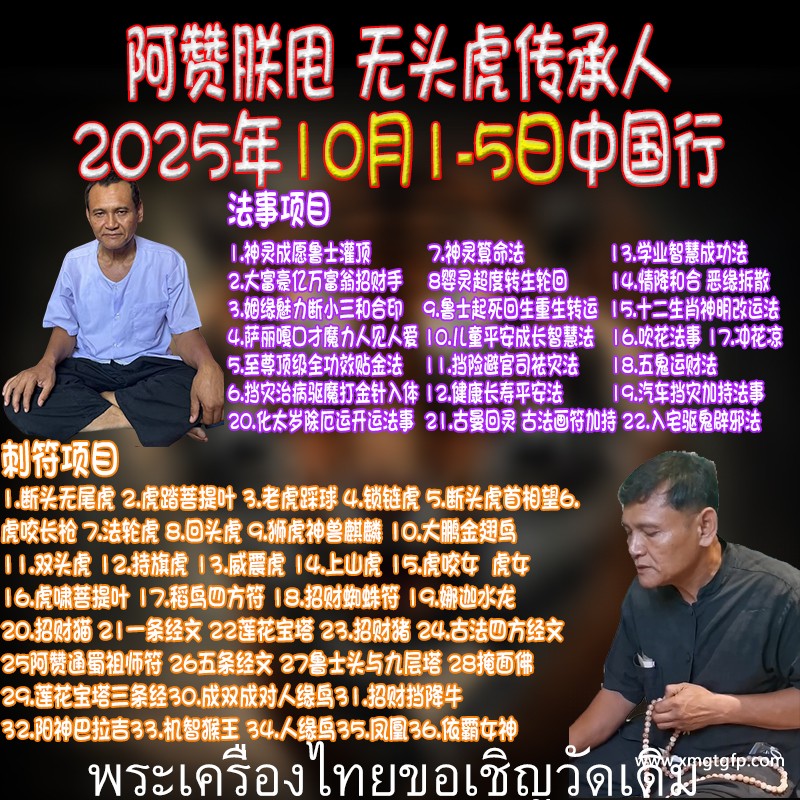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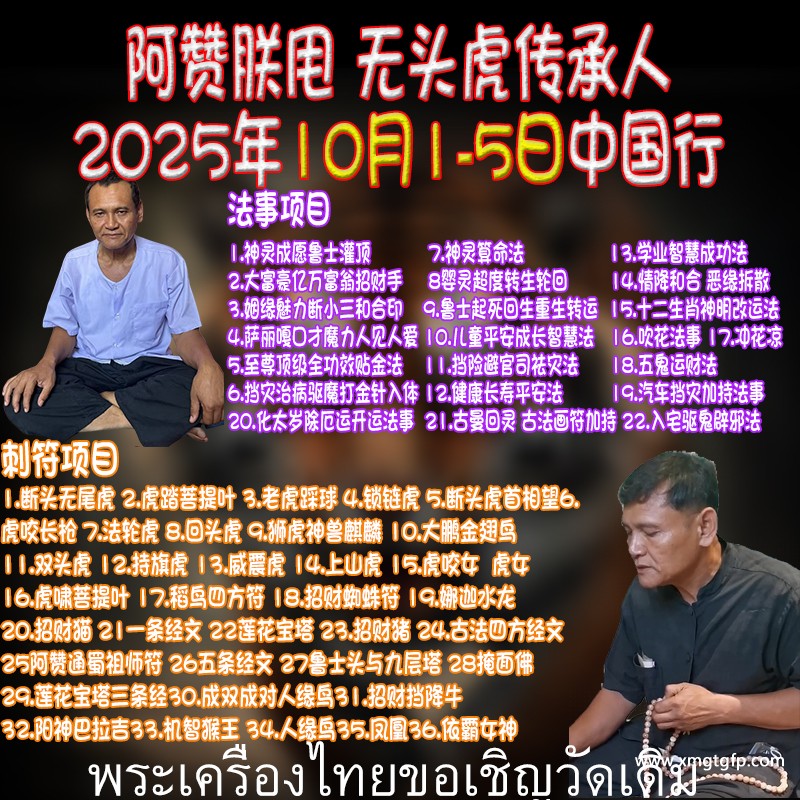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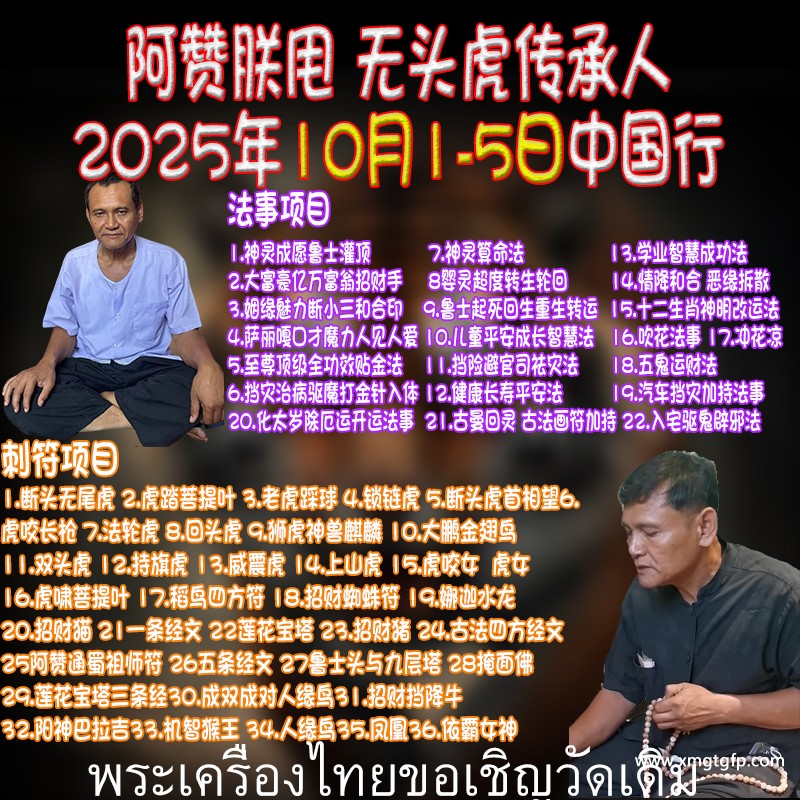




 在线客服
在线客服 在线客服
在线客服



